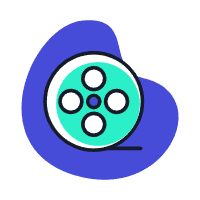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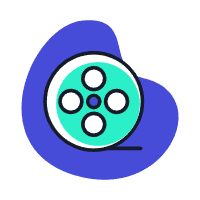

《锦绣芳华》5集追平,超爱,女频古装剧如果天天这么卷,本观众还不得乐死。
这篇也不是啥面面俱到的剧评,优点太多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就简单聊一点观感。
一,将“公共话语”归还女性
何惟芳,大唐女子启蒙实践家,从深宅牢笼中来,心怀自在向往,希望天下女子皆自在皆开怀。
她的芳园,是很典型的中古城市公共空间,她发现粟米有问题、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她虽一度被锁深闺,虽主业只是花匠,但某种程度上,一直为底层女性走出私域、进入平等的公共话语中而努力。

花鸟使,我愿称之为庙堂侠客,以骂名为遮掩,心怀清平大梦,假装蝇营狗苟朝堂污垢中,实际是王朝中期弊病的改革者,以少年侠客式的理想、寄望于源头清水赋新篇。
都爱钱爱酒爱肉,都在红尘中活得热烈畅快;
也都见不得不平事,要在黑夜里点一盏不一样的灯,像暗夜中的盗火者。

何惟芳凄风冷雨中持剑护蒋府,孤身悍然对前夫、对恶狗、对骄兵,她是女子们的精神花匠,也是她自己的刀剑。
身为盾、泪为光、气如虹,黑云压城也不惧不退不妥协,怎么不是了不起的女英雄呢?
她和蒋长扬,互为刀剑、互为铠甲,能够为对方的也是共同的美好理想战斗,是彼此精神火种的恒温箱,更重要的是,蒋长扬这份“私人情感”中,归还了对女性公共身份的尊重。

他们目前仍是恋人未满、知己以上的阶段,但处处以这种“公域尊重”为前提,比如那段剪发如同心。
《国色芳华》婚礼,蒋长扬一片真心置于发丝中,奈何对方不肯结发;《锦绣芳华》何惟芳牢狱归来,蒋长扬体贴当Tony,满心柔软但手艺不精,一缕乱发拽不清,喜提一剪梅。
手握一缕青丝,且叹且慕且无言,成年人该干的啥也没干,但恰恰有一种高级的情浓意浓。

整个过程中何惟芳侧身而坐,二人几乎没有眼神交流,蒋长扬细细擦着头发,说着你在外面是店主是姐姐,唯独深夜才可卸下一点。
新婚尚未婚,语淡情意深。
字字不提爱,但句句掏心掏肺,很体己话。
这比“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在乎你累不累”还多一层,没有“女子本就不该抛头露面”的偏见,没有“我这么有权有势会贪钱,你何必忙生意”的包办和越界。
而是尊重、支持、体恤,三位一体。

这种“尊重、支持、体恤三位一体”的情感表达,常常被规训为女性对男性的贤内助支撑,却较少正向出现在男性对女性的亲密关系表达中。
封建语境下,“贤内助”这个词,褒奖中暗含捆绑。但蒋长扬这段,恰恰打破了贤内助隐藏的规训脉络,回到贴心的行为本身。
这也不是性转埋汰男性,而是剥除结构性束缚的侵蚀,回到尊重和体恤本身。

我觉得很可贵的,是在爱的私域情感之外,首先有“公域情感的尊重”为前提。
言情故事的传统讲私人爱恋,这没毛病,但无形中也是将人压缩回私宅局限中。
古老的男尊女卑结构下,女性在公共空间和公共事业中时常隐形,既然缺失公共身份,又何谈对这一公共身份的情感?
女人爱男英雄,很古老、很天经地义,但男人爱女英雄,有点失语。
而蒋长扬对何惟芳,不仅仅是对私心的爱人,还是对一个公域的广义上的女英雄。
不仅是蒋宅里的小花,更是万里河山中的何惟芳。

二,利“她”性升华
我们何惟芳,简直为长安女子的就业率操碎了心。
前有帮胜意帮锦娘,活脱脱一个“民间就业办主任”(bushi),如今又希望为莲舟谋一份“不必在深宅依附男人争宠”的工作,主打一个走到哪里、offer发到哪里~
别人干的是抢男人的宅斗活计,而她恨不得直接拆了宅斗的深宅高墙,有一种利“她”性的升华。

她的芳园,甚至有几分像“她之理想国”,她们的乌托邦。
何惟芳帮小春行医,要面对的是观念牢笼。
广义上也是反父权,但和刘畅他爹那种森冷吃人的父权不同,小春面对的是父权和亲情的搅拌桶。
她的老父亲很爱孩子,但囿于时代偏见,觉得女人抛头露面行医被人耻笑,觉得女孩子好好嫁人才是正路,他所代表的,是爱而不见、亲而不解,相见不相知、相伴不相识。

观念牢笼的可怕之处在于,不平等不是一道诏令,除此之外处处不存在,而是处处皆在,显性隐性出现在一切毛细血管中。
典型的旧式东方家庭结构,在亲情之外,又被深深根植了尊卑等级。
何惟芳如何能荡平所有偏见呢?
但牢狱中用身体护住小春,有勇有谋有队友、终得清白出狱,四舍五入,是头破血流在偏见牢笼撞出一线天,照进一点光。

何惟芳企图帮莲舟,帮诸多被困被践踏的女子,要打破的是生存依附牢笼,是“第二性”的牢笼。
宅斗的你死我活模式,是吊在男人这一棵树上,将全部生存空间、挤压在别人的恩宠中。
而何惟芳试图往外走、往上走、往未来走,在后宅之外,开出无数新路,是暗夜女书中的启蒙者。
她对莲舟,走出了互撕模式,是后“撕”时代的助她性攀登,一如我之前所写,沿用利益冲突的结构,但走向的是价值解放的高地。

而最大的困境在于,何惟芳始终要面对最深的一层,阶级牢笼。
富甲洛阳的商女,在尚且不是顶级权力的刘家面前,都是随时可以被敲骨吸髓的血包、随时能被踩死的小蚂蚁。
贵人们不穿的衣服,平民买来穿也是僭越、也是死罪。
何惟芳第一次见宁王是狩猎,而她若被一箭射死也是她擅闯皇家围猎的罪。
种种不平事,是未来何惟芳、蒋长扬真正风雨同路的基石,这不是一个攀附强者的故事,而体现出一种消弭身份沟壑的美好愿景。

当然,无论故事如何映射现代观念,何惟芳和蒋长扬都不太可能在大唐语境下,实现绝对的人人平等,可那愿景和方向依旧可贵。
三郎和蒋长扬,一直筹谋针对宁王的大动作,那也不仅仅是针对一个恶人,而是要肃清一种风气、重建一种更健康的朝堂生态。
我们知道帝制王朝发展到中期会滋生种种问题,有学者将之命名为皇朝中期综合症,“帝国承平带来的官僚机构膨胀问题,以及相应的权力行使方式的混乱和财政适应能力的减弱”,激扬浊清的理想有时就像“试图扯着头发把自己拎起来”一样难。
但少年天子少年臣的少年山河理想,何尝不是一种光芒呢。
就像何惟芳对她们,利“她”性升华,美好寓言本就是情绪滋养。

三,寄生型金字塔、绞杀型情感
看县主和刘畅过日子,总有种“冥婚”的死感,可能下一秒就要烧死、打死、淹死同归于尽,处处是爱意勒索和寄生绞杀。
县主对刘畅,就像她爹对她,嘴上说着感情,但或许更接近绞杀式亲密关系,把人从活生生的人,绞杀成只为满足我心愿的提线木偶。
县主很靠近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但她又只是尴尬寄生于边缘,随时会成为父亲拉拢别人的工具,成为夫君嫌弃的毒妇、无用之妇。

她越受害、越沦为牺牲品,就越想践踏、越要通过压制伤害别人,来确认自己的金字塔身位。
她不觉得吃人的金字塔结构有问题,而一再只想通过绞杀、来加深自己的寄生牢固性。
她屡次要杀何惟芳,与其说这依旧是雌竞范本,不如说是权贵对平民的绞杀模式。
与其说这是性缘脑,不如说是阶级脑,她需要通过践踏自由盛放的商女,来平衡自己被锁成黄金木偶的悲苦。

当初何惟芳在刘家时,一度与她联手,但何惟芳真正的精神橄榄枝,她接不住,她早已丧失了爱和自由的能力。
她如今还真心喜欢刘畅吗?那种变态控制,很难叫爱吧。或许她怀念在是非之外的自己,她将不可追的往日,当人间桃花源来投射。
她恨的只是何惟芳吗?或许是这个世界不如我愿吧。她在牢笼中已经太久,她仗势欺人也已经太久,久到她从被困的笼中鸟,变成了沉重的笼子本身,变成了枷锁本身。

她和刘畅,都是在权力中被异化的悲剧,都像受过某种情感宫刑,或者说精神的宫刑,人格和价值上的宫刑。
如果说何惟芳和蒋长扬是上扬的美好理想,县主和刘畅则是惨痛的帝制权力疤痕,几明几暗,共同交错出悲欢离合。
一组在淤泥互相纠缠,在所谓捷径中饮鸩止渴。
另一组,赠你明月赠你清风,万里长路关关难过步步危机,种桃种李种春风,风霜与共、芳华与共。

「狗头萝莉」的故事
5600资讯2025-11-20
《误杀3》曝片段 刘雅瑟张榕容传递女性互助力量
4329资讯2025-11-20
《操纵者》上线,张子健刘威葳主演,抗日谍战剧,走爽剧路线
4050资讯2025-11-19
《暗夜与黎明》今晚收官 陈哲远聂远邢菲姚安娜共展初代公安风采
3621资讯2025-11-20
《香水佳人》首播,女性苦情剧,一妻一妾的悲惨生活,适合老年人
2928资讯2025-11-20
葛优“好人团”好事连连看!《爆款好人》正式上映
2863资讯2025-11-18
登春晚一夜成名,56岁在异国离世,临终前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2822资讯2025-11-20
EXO金钟仁将于5月11日入伍 将于2025年2月退伍
2541资讯2025-11-19
苗苗崩溃痛哭,郑恺被全网痛骂:别装“好男人”!
2494资讯2025-11-20
SEVENTEEN夫硕顺将于2025年1月初回归 目前正在积极准备中
2249资讯202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