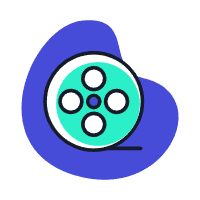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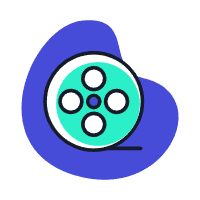

B站真的是个宝库,非常喜欢的一部经典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悄悄上新了第三季。
这部纪录片3年磨一季,季季豆瓣9.0分以上,还一季高过一季。
第三季没有胡歌配音的加持,竟然还收获了9.4的超高分,在情理之中又超出了我的预期。

现在咱们一提到读书,很容觉得枯燥和犯困,在手机短视频的冲刷下,不得不承认,成年人基本都丧失了阅读长文的能力和耐心。
但看这一季的《但是还有书籍》,真的一下子让我找到了当初没日没夜掉在书堆里的那种初心。
纪录片极为用心地挖掘出了书籍与背后人们的趣味与可爱、想象力与活力:
县城的农民大叔在二手书店淘武林秘籍,经济条件窘迫,却仍然笑呵呵地在书籍里寻找大侠梦。
北京的保洁阿姨兼职写鬼怪故事,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她就在书中主宰笔下人物的命运,觉得自己仿佛“上帝”。
这些在生活重压下的人们没有怨气冲天,书籍给了他们跨越现实、笑得出来的蓬勃朝气。

在这些平凡的爱书之人身上,有一种发自内心对书的好奇与珍惜,阅读已经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本能。
“一本书从来没被人看过,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活过一遍。”

近朱者赤,读书氛围越来越稀薄的当下,去看看一群用生命爱书的人,也许会重新收获阅读一本书的感动和行动力。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爱书人的奇幻世界。
01
书籍是有趣灵魂的大型玩具
书对有些人来说是谋生的工具,但对有些人来说更像有趣的大型玩具。
有些爱书之人会像“淘金”一样,奔赴各地挖掘珍宝,再让有用的书到达心动的读者手上,遗忘的书籍重获新生,他们乐此不疲。
河北霸县的一家二手书店永丰书店,就是这样一个“宝藏”藏书阁。
除了畅销赚钱的教辅材料,店主老刘更热衷于售卖从天文地理到农林牧渔的“奇珍异宝”。
县城没人能看懂《弹道导弹与运载火箭》他因为喜欢还是从北京大老远运了回来。
《少林绝命腿》一度被他视为视若珍宝,他曾偷偷默默想要练成盖世武功,如今多年未练,已经有些荒废。


即使是贫穷的小县城,也有不少跟他一样的身怀各种梦想的“普通人”。
书店收藏了几十种武侠小说,十里八乡有点武功绝活和痴迷武侠的人都来他这些交流切磋。
喜欢国画的农村老大爷,一直纠结怎么把人物画得惟妙惟肖,书店里的水浒传人物卡就成了他的珍贵教科书。
这位镶了满口银牙的大爷,隔三岔五就要来寻宝,走的时候总是收获颇丰,笑意盈盈地满意而归。
越是书籍贫乏的时代和地区,越是能找到嗜书如命的人,因为有种叫做珍惜的感情在推动着他们搜寻。
30年了,每周老刘都孜孜不倦地从北京潘家园旧书店搬运一面包车的精神食粮回到贫瘠的小县城。


与这个店主不同,另一个打工人白天迷迷糊糊地做着养家糊口的编辑主业,下班了才开始精神抖擞地投入副业。
说起侦探故事,西方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几乎艳压所有的侦探小说,直到华斯比翻开了旧的发黄的民国侦探小说,竟然发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国侦探宇宙。

《胡闹探案》是带他入坑的第一部小说,里面的主角胡闹简直是一个“失败学”代表。
所担任的案子没有一桩不惨遭失败的,对眼皮子底下的凶器视而不见,把晕倒少女误判成尸体,但因此也抖出了不少包袱,让读者哭笑不得。
这种反成功学的写法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先锋的,但是却因为各种原因还是被遗忘在历史黑暗里了。
华斯比就是坐船去黑暗长河里打捞这些绝版侦探故事的侦探。

宅男的他踪迹却遍布各大线上线下民国二手书店。
生活可以拮据,但是买侦探书绝对大手大脚。
如果因为手慢旧书被别人抢走,那叫一个心疼自责。
渐渐地打捞地越来越多,他摸索出了民国侦探宇宙的更多脉络,开始孤注一掷地系统整理和出版民国侦探系列丛书。

尽管很多人说他在做无用功,但是在华斯比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读者看到了中国侦探小说世界科学与趣味齐鸣的辉煌历史。

“我觉得我其实是个笨人,可能因为比较笨,不像人家有很多方面的成就,我就想在我认准的这条道上走到黑,可能历史记住的是那些大人物,像我们这些小人物也希望被历史记住。”
他们从趣味性入坑,却带着使命感帮助书籍也帮助自己穿越了默默无闻的黑暗时光。
02
阅读是人生可能性的放大器
读书给人的可能性远不止考试升学、高谈阔论那么简单,任何人在书籍的加持下都可能跨越别人设置的边界。
在北京大街小巷各处找零工的家政阿姨范雨素还有另外一个隐藏身份——非虚构作家。
之前一篇《我叫范雨素》的自传式文章突破400W+的阅读量,让这个家政阿姨出了名。
她没少干过这种“出名”的事。

12岁读《唐吉可德》,她给家人留下一句“赤脚走天涯”就有了现在很时髦的出走的决心,一路从湖南逃票坐火车到了海南。
然后课本里说鲜花四季、水果遍地的海南却没有让她果腹,无尽的饥饿把她逼回了原地,却落了一个“私奔”的坏名声。
这种女性羞耻感陪伴了她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被人指指点点的另类。
多年后才却意识到如果是一个男生这样,大家只不过觉得他走了趟亲戚那么平常。
20岁,受《鲁滨逊漂流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影响范雨素继续去冒险家的乐园——北京探险。

稀里糊涂地,她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男人结婚,婚后男人仅仅是因为不高兴就对她拳打脚踢。
范雨素形容那是比书中地狱级苦难还要苦的,她义无反顾地跟男人离婚,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
她给别人做月嫂、育儿嫂,假装幸福快乐地抱着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成了“孤儿”,小小年纪的老大负责照看更小的老二。

如果不是因为大量阅读,她铁定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做单亲妈妈的。
单亲妈妈真的很苦很苦,一边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饿死,一边下户之后还会被雇主诬陷偷了她家的书。
可这种勇气不仅让她挨过了最恐惧的时光,还让她拒绝了20万现金的稿酬诱惑。
因写自传文章出名了,有出版社来找到她再写本非虚构小说。
她却放弃了咸鱼翻身的机会,笔锋一转,开始写《久别重逢》,一本写家乡荒诞迷梦、鬼神传说的虚构小说。

拿起笔她仿佛像创造人类的“上帝”,可以主宰书中人物故事的命运,漂泊不定的她享受这种感觉,也在努力为自己的人生掌舵。
“我知道自己一生的命运都过得不好,但我依然要面对自己的命运呀,生命就是要努力向上生长的呀。”
范雨素没有文凭,但是阅读和写作就是她的帆,带着她去远方,也支撑她与风浪周旋。

同样在阅读和写作中找到避难所的还有66岁的作家林白。
30年前女性主义还不行盛行的时代,她就在写女性内心幽微世界,作品可想而知被男性评价体系忽略。
被批评不看好的岁月,她依旧坚持,依旧相信避难所不是家乡也不是异乡,而是写作以及不断阅读写作的自己。

那些少年深入人心的故事,依旧可以在多年之后为她加油打气,这就是阅读的意义。
03
阅读不只翻书一种形式
阅读不只翻书一种形式,所有好奇心、探索欲驱使下的探索都可以称得上是阅读。
一群走在“田野”里的人,用脚步和倾听先为读者“读”了一遍世界。
盛文强一个生在东南沿海,搜集东南沿海故事,为传说中的海洋妖怪立传的人。

从小在海边长大,盛文强沉迷于各种异闻奇事。
顺风耳和千里眼原本是两个海怪,被妈祖娘娘降伏以后,就收入了编制体系,位列仙班。
这些都是正统妖怪,还有很多非主流妖怪。
比如传说中白天伪装成普通渔民,夜半离体觅食的飞头獠,从熙攘人群头顶呼啸而过化身海怪坐骑的铁锚,还有长相丑陋又内向羞涩,能用自己的光头照亮夜航船每一个角落的海和尚。

书写妖怪,是中国自古有之的传统,但是关于海怪却大都是面目模糊的,盛文强励志一定要填补这一空白。
他奔走各地把散落民间的妖精魔怪碎片打捞整理出来,为本土妖怪搭建起一部中国妖怪的家谱《何方妖物》。
不仅如此,他还走进渔民家庭,从渔民与海搏斗的记忆中了解“真实”的海怪,同时试图还原鬼神传说下光顾陆离的渔业社会。
渔民所用的传统的龙裤(渔民的一种工服)、渔船、渔具、绳结看似普普通通,其实也充满了奇妙的劳动智慧和故事。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原本支撑一代又一代人的传统技艺及记忆正在消失,盛文强又一点点收集、系统整理成一本《渔具列传》,为其留名。
但也有很难破解的民间传奇,比如广泛留存在闽浙边界山区的编木拱桥。
这是结构工程师都算不明白的、算不清楚的一个奇迹。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出身的刘妍注意到了编木拱桥,就一直把它当成研究课题在解决。
他花了12年的时间追踪调查了中国现存的110多座编木拱桥。
却发现接受过数学、力学、工程学等系统科学训练的自己还是无法解释很多问题。

刘妍意识到只有真正造一座桥才能明白一座桥。
他开始跟随当地造桥世家吴大根师傅学习,造桥师傅不会力学计算,但是他们内部传承着一套秘密计算公式,实际情况还需要依赖匠人的眼力与经验随机应变。
这些都是刘妍在文献和老师那得不到的,只有跟造桥师傅同吃同住才能获得。

吃苦耐劳的刘妍经过了造桥的考验,他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物理的编木拱桥背后还有更复杂的人与生活,资金的筹备、技术的传承、经济的发展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建筑系的刘妍又投入到人文社科领域,走访周边村落,结合家谱、桥梁上的墨迹,梳理编木拱桥背后经济和技术上的依赖与传承。
田野在学术上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其实它更是一种阅读方法,是一种好奇心与探索欲驱使的世界观。
我一直有个体会,如果真的把阅读当个“事”要去做,难免会产生厌烦心理。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但这难度之大家长也能从自己的阅读经历里体会到。
纪录片中的独立译者小何便是如此,她小时候也是一个厌恶阅读的人,因为总觉得那是家长布置的任务。
直到她长大,从书籍中感受到了快乐,才发现阅读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狗头萝莉」的故事
5649资讯2025-12-20
《误杀3》曝片段 刘雅瑟张榕容传递女性互助力量
4394资讯2025-12-20
《操纵者》上线,张子健刘威葳主演,抗日谍战剧,走爽剧路线
4103资讯2025-12-20
《暗夜与黎明》今晚收官 陈哲远聂远邢菲姚安娜共展初代公安风采
3684资讯2025-12-20
《香水佳人》首播,女性苦情剧,一妻一妾的悲惨生活,适合老年人
3008资讯2025-12-2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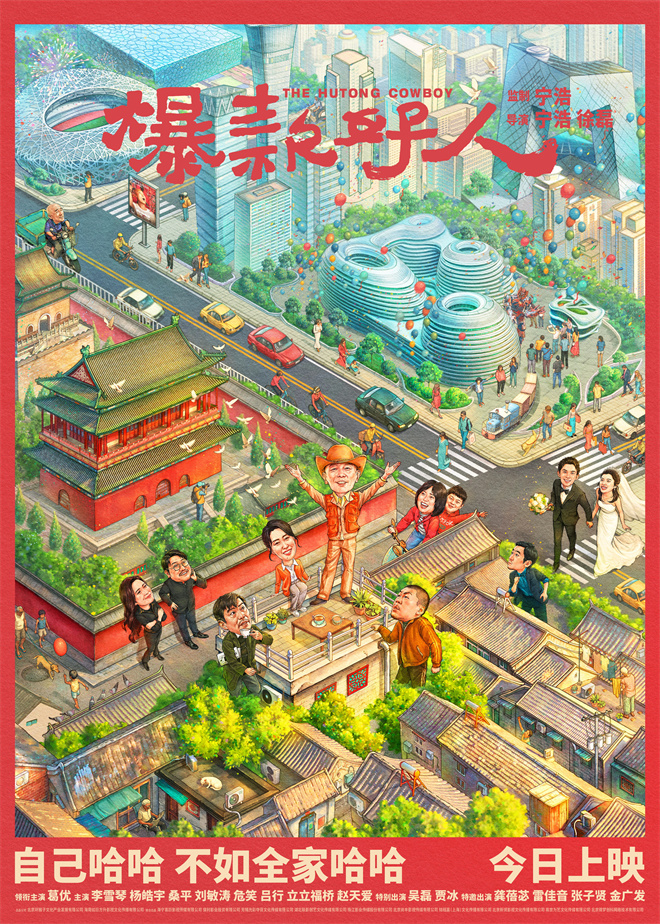
葛优“好人团”好事连连看!《爆款好人》正式上映
2932资讯2025-12-20
登春晚一夜成名,56岁在异国离世,临终前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2887资讯2025-12-20
EXO金钟仁将于5月11日入伍 将于2025年2月退伍
2611资讯2025-12-20
苗苗崩溃痛哭,郑恺被全网痛骂:别装“好男人”!
2527资讯2025-12-20
SEVENTEEN夫硕顺将于2025年1月初回归 目前正在积极准备中
2311资讯2025-12-20